星空体育官网-巴拉圭女足在南美女足杯中表现出色,成功挺进四强
编者按
上海交通大学社会认知与行为科学研究院(筹)与“社科法学连线”定于2017年6月18日(周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法律与认知”工作坊。现推送与工作坊相呼应的“认知系列”。
虚假口供是众多错案形成中的关键。为何无辜者的辩解无人相信?除去干扰因素,或许警察辨识陈述真伪的能力并不像人们通常期待的那么高。原标题《无辜者何以被怀疑?——警察辨别真伪陈述能力的认知-行为研究述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推送时有修改。
无辜者何以被怀疑?
——警察辨别真伪陈述能力的认知-行为研究述评
文 | 林喜芬,葛 岩,秦裕林
如何运送司法正义,防范司法错案,这从来都是一个热点议题,也关系着一国刑事法治的基本水平。1990年代末至今,随着中国诉讼制度的规范化,刑事司法经历了理念更新、程序改良和技术提升等多重进步,而发生于2000年左右的杜培武和辛普森案为中国学界对勘中西司法制度提供了上佳样本,随后的佘祥林、呼格等冤案正好成为学界批判实践、拓展改革和借鉴域外经验的切入口。在政策上,鉴于司法错案影响到社会正义和司法权威,高层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重点提及了司法错误的防范、救济和纠正。在学理上和实务中,法学领域中对错案成因或相关因素的分析更多地停留在制度层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刑事案件的亲历者——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的记忆偏差,强烈的办案诱因,伪科学和虚假鉴定,适用法律不当,始终相信警察诱供、刑讯等是造成错案的主要原因。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撑了这些判断。
图:呼格吉勒图
基于错案样本的简单统计,研究者发现错案中存在侦查不当,被告人虚假口供的占96%,存在虚假证人证言的占94%,存在鉴定缺陷及鉴定结论错误的占28%,存在忽视无罪证据的占20%,存在审判不当的占18%,等等。但在此其中,关于认知因素(如认知偏差或扭曲)的分析却基本缺席。不仅如此,在错案分析过程中,对于无辜者被定罪的原因最容易引发学者的关注,对于无辜者被怀疑并被纳入诉讼的机制,则缺乏深入研究。
事实上,侦查工作不是无缘无故展开的,也不会漫无边际地进行。为何要确定他(无辜者),而不是他(罪犯)为嫌疑人,并将之纳入侦查?为何确信他(无辜者)是关键嫌疑人,并进行重点侦查?为何又选择对他(无辜者)加大审讯力度,乃至非法取证呢?从侦查者的角度讲,总会有一些事实依据或经验常识,至少存在若干或不易表达清楚,但却感觉应该如此的认知逻辑。例如,该人在被询问或讯问时,紧张、焦躁不安、神情恍惚,有不寻常的动作,词不达意或前后矛盾,等等巴拉圭女足在南美女足杯中表现出色,成功挺进四强;此时,若尚有其他一些证据指向该人,该人被推测为嫌疑人,进而着意获取与此推论相关的指控证据,对之重点对待,最终对之定罪判刑的可能性增大。有理由相信,在此过程中,将某人认定为嫌疑人这一初始判断至关重要,而一旦将其确定为嫌疑人,在后续侦查、起诉、审判程序中,司法人员很可能会受证实偏见和不合理的制度激励的影响,抱持有罪推定的思维,最终导致错案发生。然而,这一初始判断到底认知精确度有多高?如若很高或较高,就有利于提高侦查效率巴拉圭女足在南美女足杯中表现出色,成功挺进四强;如果不高或较差,则侦查人员就必须时刻反思,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也应对之警惕。
对于警察经验判断的准确性,社会公众往往操“两可之说”:当某一特大案件被侦破时,基于直觉或经验而锁定嫌疑人的侦查人员往往被推崇为“神探”,立功嘉奖自然少不了;而当某已决案件被发现存在瑕疵或错误时,同一侦查人员又被斥为制造冤狱的“坏人”。法学界对此并未给予更充分的解释。显然,这种评估方法并不符合社会科学的标准。相反,近年来,以认知-行为实验为基础的刑事司法科学研究提供了相关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关于侦查人员认知精确度(尤其是在辨别真伪陈述时)的知识。
本文主要目的是梳理与评析域外认知-科学研究(限于语言,集中于英语世界)的一系列成果,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通过观察嫌疑人的非语言行为来甄别嫌疑人是否说谎,有效吗?2.侦查人员的经验或培训对于甄别嫌疑人是否说谎,有帮助吗?3.哪些方法可能提高人们(尤其是侦查者)辨别真假陈述的能力?4.域外此领域的认知-行为科学研究,对我国法律界和法学界有哪些启示?
一
讯问的重要技巧:重视嫌疑人的非言语行为
无论能与不能,日常实践(尤其是专业领域的实践)中,人类都在试图识别谎言。对于刑事司法而言,如何识别谎言,去伪存真,并进而查明案件真相,解决刑事法律纠纷,乃是其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域外,在侦讯领域以外,一些研究发现非言词行为能够提供大量信息,可用于甄别陈述的真伪性。如Paul·Ekman发现,人试图掩饰的情绪会在1/15秒的一瞬间在面孔上表现出来。他汇总了一份“微表情大全”,即“脸部动作编码系统”,相信通过这个系统,找出与被测人面目表情相对应的情绪,就可以辨别其是否在撒谎。在刑侦领域中,最流行的,同时也非常强调非言词行为重要性的审讯方法,乃是Inbau,Reid和Buckley提出的“雷德审讯法”。这三位教授在1986年编纂的办案手册——《刑事审讯与供述》中系统提炼了该方法。基于该方法,芝加哥研究室的John·E·Reid和他的同事们通过讲座、研讨会以及视听课程教授刑事执法人员如何运用雷德审讯技术开展询问或讯问。雷德审讯技术建议,讯问者可让嫌疑人坐在一个狭小、隔音、简陋的审讯室中,创造一种使嫌疑人产生社会隔绝感、被剥夺感、无助感的物理环境;进而,建议执法者向嫌疑人施加一系列社会影响,令嫌疑人正视自己的罪过,同时,执法者拒绝接受嫌疑人的无辜陈述和辩解,但须表达对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同情和理解;然后,让嫌疑人以书面的方式重述自己的犯罪经过。根据Jayne的描述,这种方法旨在通过减轻嫌疑人对供述罪行导致的负面结果的感觉,以及强化其说谎时的焦虑感,从而实现让有罪嫌疑人自白或者帮助审讯者辨别真伪陈述的目的。
在我国刑侦领域,诸多学者都认可非言词行为能作为辨别嫌疑人陈述真伪性的信号的看法。一些法学学者从“五辞听讼”的历史意义出发,认为“从古代关于‘五听’的理论及运用‘五听’方法破案的实例看,不少对我们现在的审判活动依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更多的刑侦专家秉持以下立场:其一,非言词行为是言词行为的基础。侦讯中的言语交流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其信息的真实性往往大打折扣。因而,非言语交流传达的信息量多达70%。其二,嫌疑人无法控制非言词行为。“对(嫌疑人)自己的非言语情态,他们虽然也会极力掩饰,但其与生俱来很难控制的特点,使这类掩饰非常笨拙,时常弄巧成拙,反而泄露了心中的秘密。而当疑犯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相矛盾的时候,侦查员一般都会本能地相信疑犯的非言语行为传达的信息。” 其三,特定的非言词行为能说明嫌疑人的陈述是虚假的。“一个不敢与审讯人员的目光接触的嫌疑人可能是不诚实的”,“最常见的语调方面的欺骗迹象是停顿,如停顿得过长或者次数太多;破句也可能是一种欺骗迹象,如夹入无意义的语音‘呃’、‘啊’、‘嗯’”;“关于语音的情绪特征,最引人注意的是音调,有人做过研究,大约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情绪不安时说话的音调升高,当不安情绪是愤怒或者恐惧时,这一结论可能最为准确,一般说来,愤怒或者恐惧时人说话比较响和比较快、悲伤时说话比较轻和比较慢。”在刑事政策上和审讯实务中,有对抗情绪被理解为“不老实”,眼神游移被理解为“耍滑头”, 坐立不安被理解为“做贼心虚”,回答存在矛盾被理解为“虚与委蛇”,则是常见之事。
二

警察辨别真伪陈述的有效性:域外的实验结论
使用非言词行为来判断说谎的准确度究竟高不高?上述基于常识的观点符合科学原理吗?在相关研究中,虽有一些研究采用了实验方法,证实了某些表情可以用于判断说谎与否,但是,一般人和专业人在基于表情判断时,是否可以达到很高的准确度呢?在域外,为数不少的实验研究表明,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其实很差。以Charles·Bond的研究为例,他调查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千人,请他们讲述自己怎样通过行为举止识别他人是不是在说谎。结果显示,被测者的识别准确度不仅很差,而且,他们的回答惊人地相似:不论是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德国、加纳、巴基斯坦和巴拉圭,几乎所有国家的人都认为,说谎者常常避免与你目光对视,紧张地摆动双手,并且在椅子上挪动。Bond发现,人们不能识别谎言,是因为他们根据那些实际上并不能与说谎相关联的举止来形成判断。在一项与O'Sullivan教授合作的研究中,他们试图在12,000被试者中寻找所谓的高手,结果发现,只有29个人识别谎言的情况符合高手的标准。这一比例可能随机出现,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实现高精确度的辨别真伪的标准并不清楚。这意味着其他人无法从中汲取经验,以便模仿。刑事司法(尤其是审讯)工作,与日常生活实践相比,恰恰以辨别真假陈述为核心内容。警察及其他所谓调查专家长期以此为业,情况是否会不同呢?注重观察嫌疑人紧张、恐惧等非言词状态的雷德审讯技术,在甄别嫌疑人有没有说谎时,是否有效呢?具体而言,罪犯和无辜者的非言词行为会不同吗?用言词信息佐证非言词信息并进行说谎判断,有效吗?对比观察非言词行为和聆听言词行为,哪个更有效呢?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中,通过非言词行为来辨别陈述的真假,是否更容易呢?警察的辨真精确度比大学生及其他群体更高吗?经验丰富的警察比经验少的警察,辨真精确度更高吗?
1.使用非言词行为来判断陈述的真伪有效吗
(1)罪犯与无辜者的非言词行为会不一样吗?Kassin和Fong在1999年检验了人们能否发现被试者在否认某一“犯罪事实”,利用言语或非言语的欺骗线索对警察所进行的培训能否提高他们在此方面的判断准确度。在实验的第一阶段,被试者先实施四个模拟的犯罪行为中的一种,然后在接下来的讯问中否认他曾参与这一犯罪行为。在实验的第二阶段,观察者分为两组,一组经“雷德审讯技术”训练,另一组则未经训练,然后,让两组观察者分别去观察这些模拟讯问视频。就像其他研究所揭示的一样,被试并不能准确区分说真话的和说假话的“嫌疑人”。事实上,过培训的一组被试辨别的准确度更低,但却表现得更为自信。Ekman&O'Sullivan的研究显示,测谎仪操作员,精神病专家,抢劫案侦查人员等专业群体在识别谎言方面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他们判断精确度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更注重嫌疑人的非言词行为,因为那些被错认为说谎了的诚实陈述者往往表现出与说谎者类似的恐惧类型和行为模式。正如Simon所指出的,“紧张、恐惧、困惑、敌对,改变所陈述过的故事,或所陈述故事存在矛盾,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审讯室中嫌疑人说谎的信号,在那些本来就充满怀疑的警察眼中更是如此。然而,不幸的是,这些非言词行为同样也是人在高压环境中或紧张状态下所发出的信号。”
(2)使用非言词行为并结合言词行为有利于辨别真伪,排除无辜嫌疑人吗?答案似乎也是否定的。在一项实验研究中,Aldert·Vrij el al使用20对说谎者和20对说真话者,让其准备接受询问,回答诸如特定时间在哪里时一类问题。研究显示,与说真话者相比,说谎者更可能准备如何回答讯问。而做了准备的说谎者和说真话者,准备使用的言词策略有所不同,但非言词策略却是一样的。关于言词策略,说真话者更可能会考虑将所有相关记忆尽量全部说出;相反,说谎者则会考虑哪些回答可以应对可能的问题,同时,仅以模糊的方式回答,以避免相互矛盾。这解释了真话的内容为什么往往会比说谎的内容的更加具体。同时,说谎者在叙述连贯性上与说真话的人差不多,至少,在回答那些说谎者已经有预期的问题时如此。关于非言词策略,说谎者和说真话的人都会试图避免紧张动作。这一研究表明,反侦查乃是罪犯的天性,罪犯应对讯问的技巧往往给侦查人员辨别真假造成较大的困难。不仅如此,与嫌疑人相比,无辜者的相对“无知”经常为警察甄别真伪陈述制造了障碍。因此,谁为真(犯罪),谁为假(无辜)并不容易被甄别清楚。在侦查初期,在证据信息非常有限,在客观证据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3)观察非言词行为与聆听言词行为,哪种更有利于辨别真伪,排除无辜嫌疑人?有意思的是,非言词行为所给予的判断信息,或者基于非言词行为的判断标准,其可靠性甚至还不如聆听嫌疑人的言词。Maria·Hartwig et al的一项实验研究以30名有经验的警察为被试,测试其辨别真假陈述的能力。研究者让被试警察讯问那些在模拟犯罪场景中有罪或无辜的大学生被试,并对被试是否说谎的判断。一组警察可以对大学生实施在他们认为合适的讯问。这些讯问行为被录下来,交由另一组警察观看。实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在真实场景中讯问的警察,还是通过观看视频判断嫌疑人是否说谎的警察,其辨别真假的准确度都不高于50%,即与乱猜结果相符的随机概率。
(4)在高风险环境中,通过非言词行为辨别真假陈述更容易吗?
O'Sullivan,Frank,Hurley和Tiwana的一项元分析研究显示,在23项涉及8个国家的31个不同的警察对照组的研究中,当用来检测警察官员的谎言样本是高风险环境(例如,谎言是自我卷入的,且(或)说谎者可能获得较大奖励或惩罚)时,警察官员的辨真能力就会比较强一些(67.15%);当测试这些警察官员的谎言样本是低风险环境时,精确度就相对较低(55.17%),两者差异具有显著性。当然,针对O'Sullivanet al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观点,如Aldert·Vrija和Pranders·Granhag指出虽然审讯环境的风险程度与警察被试的辨真能力可能会存在相关性,但是,其相关程度可能并没有O'Sullivan所指出的那么高。总体上,两者环境的精确度差距可能只有轻度的显著性。
2.有经验的审讯主体判断陈述的真伪更有效吗
(1)警察的判断精确度比大学生的高吗?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警察本身的辨真精确度高不高;警察的辨真精确度与大学生的比,哪个更高?其实,前述每项研究几乎都会涉及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因为,研究者一般都会选择两种被试——大学生和警察,并对两者进行比较。而结果往往显示,一方面,警察的辨真精确度并不高,几乎与扔硬币这样的随机概率差不多。另一方面,一些研究显示,在实验的审讯环境下,警察的辨真精确度反而不如大学生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会指出两个问题:其一,尽管警察的辨真精确度低于或不高于大学生的,但是,他们却表现出较强程度的自信,对自己的判断准确性估值要高于大学生的判断。其二,对警察和大学生的辨真精确度区分为“将有罪认定为无辜的错误率”和“将无辜认定为有罪的错误率”。结果显示,警察“将无辜认定为有罪的错误率” 更高。
(2)警察的判断精确度比其他群体的高吗?很有意思的是,一些研究还比较了警察这一审讯专家与监狱囚犯在辨别真伪陈述方面的能力。研究结果显示,在识别欺骗的能力方面,囚犯比专业人士有更好表现。他们识别欺骗的能力甚至可以和美国特工和临床心理学家相提并论。不仅如此,监狱囚犯具有更少的关于欺骗的陈规旧矩,掌握更多的与实验结果一致的关于欺骗的客观线索。例如,监狱囚犯很少把目光转移和过多的肢体动作,陈述缺乏一致性作为说谎的证据线索。
(3)经验多的警察比经验少的警察,判断精确度更高吗?很多研究发现,诸如增加练习、加强培训或者提供表现反馈等方法,并不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被试判断真伪陈述的精确度,尽管能得到一定的改进。对于那些有经验的警官,提供更多的练习、培训或表现反馈,效果也类似。
三
提高辨别真假陈述能力的可能方法
如何提高警察辨别真假陈述的能力是一个极具应用价值的问题,刑事司法无时无刻不在涉
及辨别陈述的真伪。目前,认知心理科学家也正寻求提高人们(尤其是警察)在辨别真假陈述方面的能力的有效方法。
第一,引入一种新型的“区分问题”的讯问技巧,可能有助于提高分辨罪犯和无辜者的能力。
通过讯问者对被讯问者的非言语行为的观察来辨别真伪,这是一种被动式的、非介入式的辨真方法。如前所述,之前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表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并未获得证实。一些研究者转而从主动的、介入式的讯问技巧来提高警察辨别真伪陈述的能力。研究者指出可以引入一种新型的讯问技巧,从而引出罪犯的可能说谎行为。他们建议使用一系列嫌疑人无论如何都能想得到的问题,和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问题。当同案犯之间商量要编造一个故事时,他们肯定会讨论相互之间怎么说这个故事。讯问者可以分别单独讯问这一组同案犯,当分别问他们可以预期的问题时,两者的回答应该是重叠的;当问及他们无法预期的问题时,两者的回答就可能出现不同。而对于说真话的人或一组人,在两种条件下,他们的陈述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会显著不同。
第二,一些研究显示,在讯问嫌疑人时先不让被讯问人接触犯罪细节,这样可以提高讯问人辨别真假的准确性。
M·Hartwig et al指出,以往关于辨别真假的研究大多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在讯问过程中先向嫌疑人出示了强有力的控诉证据,以让犯罪人无从辩驳的控诉证据存在。而他们的实验希望检验当讯问开始阶段先不向被讯问人出示证据,讯问人辨别真假陈述的能力是否会提升。研究者提出假设:在较晚出示证据的情况下,因为被讯问人无从知道警察掌握的证据情况,这可以避免被讯问人(尤其是犯罪人)对警察的证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反驳,从而增加了被讯问人陈述与警察所掌握证据之间的不一致性。然后,基于前文提到的De·Paulo et al(2003)的发现,犯罪人在否认犯罪时为了避免露出马脚,会以简单但符合逻辑的故事反驳;无辜者在否认犯罪时则以较复杂的、全面反映真相的方式来反驳,M·Hartwig et al指出,警察可以根据犯罪人和无辜者在否认犯罪时陈述特征上的不同,甄别真假陈述。通过使用116位被试者对58个嫌疑人陈述真伪的判断加以分析,实验结果支持了上述主要假设:较晚出示证据的一组被试者,辨别真假的总体准确率(真话被识别为真和假话被识别为假占真话假话总体样本的比例)为61.7%,较早出示证据的被试者为42.9%。对于较晚出示证据的一组被试者而言,说谎的陈述被辨别出来(假话被识别为假占假话样本的比例)的准确率高达67.6%,这显示出这一方式对于提高辨别真假能力是比较有效的。
第三,另有一项研究显示,因为说谎比说真话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通过加大嫌疑人的认知负荷(如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让嫌疑人以相反的方式讲他们的故事),询问者得以观察嫌疑人的努力信号(如犹豫等),可以使询问者做出更准确的真假判断。
第四,语言学家也做了尝试,通过语言风格来区分真实的故事和虚假的故事。鉴于说谎经常需要编造不曾经历且无法产生态度的故事,因此,与真实的故事相比,虚假的故事在质量上有所不同。研究者要求被试者在不同的语境下针对不同的主题发表真实的陈述和虚假的陈述,通过对五种主题(对着录像机录下关于堕胎问题的陈述,在电脑上输入关于堕胎问题的陈述,在纸面上写下关于堕胎问题的陈述,对着录像机录下关于朋友的陈述,对着录像机录下关于模拟犯罪的陈述)进行实验测试,并使用计算机进行内容分析,由此得出的关于陈述真伪的准确度不仅高于随机概率,也高于由人直接判断的准确度,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当主题恒定的时候,通过计算机内容得出的判断准确度会更高。此外,与说真话时相比,说谎时知复杂性降低,表现为更少引用自己或他人,使用更多的负面情绪的话。
四
认知—行为科学研究对刑事诉讼法学(律)界的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域外认知-行为科学在警察辨别真伪陈述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与我们的常识相迥异的画面。可惜的是,我国法学(律)界对认知-行为科学与刑事司法的交叉研究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也并未沿着认知分析与行为实验方法路径展开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认知-行为科学与法学的交叉研究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颇具声势的引介,但截至目前,认知-行为法学在中国更像是一种法理学思潮,而非一种可资应用的法学方法,更未在某一领域(如司法领域)产生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未达到与域外同重量级的研究水准。其实,认知-行为科学在现代西方法学领域作用最显著的领域就属法律认知与判断研究,司法证据研究等,辨别陈述的真伪仅是其中一例。
首先,上述关于警察辨真能力的认知-行为研究显示,域外此方面的研究采用最多的乃是行为实验的方法,而非单纯的常理推断或主观认定。如葛岩总结说:“认知-行为科学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实验方法。效法自然科学,认知-行为科学研究通常采用标准化的论证方式:依据观察或过往研究成果形成研究假说,围绕假说检验来设计实验或调查方案并获得数据,利用量化的方式证实或证伪假说,最终获得关于变量间关系的结论,理想状态下,是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经验导向和实验方法为澄清“警察并不具备超出一般人的辨真能力”、“非言词行为在辨真方面具有较强的误导性”等问题,提供了较客观的经验数据,也为进一步有针对性的争论提供了可能。
其次,上述关于警察辨真能力的认知-行为研究显示,诸多传统的审讯技巧和侦查经验,其有效性需要加以检验,至少应谨慎对待。如果说人们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常不能“去伪存真”, 法学(律)界还比较好接受,但是,大量实验表明,专业司法,执法人员也是如此容易“以假当真”或“误真为假”,则是法学(律)界非常陌生,不愿意接受的看法。例如,我们通常相信,侦查人员在判断真假方面是超出常人的,但这样的信念几乎无法获得行为实验的证据的支持。除了CIA等特殊的调查人员之外,警察和其他侦查人员在此方面的能力并未见超过普通人群。一些传统上被视为是可以甄别说谎与否的经验或培训技能(如注视规避,焦躁不安)反而会阻碍对说谎者的甄别。然而,无论是否情愿接受,这些实验发现说明我们一直学习的所谓“雷德审讯技术”(包括其他西方经验)可能是有瑕疵的,甚至是存在错误的,对提升办案质量可能起到反作用。
对于这些知识,法学(律)家可以使用,也可以加以反驳,“证明它们是虚假的,或,在法学领域基本无用。但无视这些知识,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却不太容易做到,因为这会显得执拗、无知。”
再次,关于警察辨真能力的认知-行为研究显示,传统关于错案的研究对认知要素(尤其是刑事侦查启动环节的认知要素)的忽视是有偏颇的。如果在案发初期,警察关于谁是嫌疑人,谁可以被纳入侦查的判断常是不确定的,很容易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那么,这一初始判断很可能成为错案之源。无论是在域外,还是在我国,警察在决定是否对嫌疑人启动讯问程序之前,都会进行讯问前的询问,而在该询问过程,警察会判断该嫌疑人是在供述事实,还是在说谎。纳入侦查后,当认定该人具有重大嫌疑时,讯问强度就会大幅提高。而询问和讯问,往往都是在没有其他客观的辅助证据支撑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是否被怀疑,是否“加大审讯力度”,基本上依赖于审讯者(尤其是对非言词行为)的经验判断。基于前文所述的实验结论,这种精确度不高的判断将增加该案成为错案的可能性。
最后,参考认知-行为科学研究的发现,雷德审讯技术及重视非言词行为的审讯方法可能存在缺陷。值得忧虑的是,若该审讯技术与我国实践中较常见的强制取证短路结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错案的风险。这种忧虑不是多余的。强制取证往往以有罪推定为前提,而雷德审讯技术,默许或认同嫌疑人的犯罪动机,缓解其对认罪可能导致的惩罚的感受,这很容易导致无辜者错误认罪;而以非言词行为为信号的审讯方法可靠性和准确度又很低,很容易导致讯问者误将无辜者认定为嫌疑人或罪犯。当两种讯问技术耦合时,就可能导致“确证循环”,即侦查者带着强烈的有罪推测,为了证实自己的错误偏见,导致讯问行为的强制性和攻击性加剧,诱发嫌疑人非寻常的紧张和不安行为,而后者又进一步强化侦查者的有罪推定,误以为是嫌疑人在供述与不供述之间游移不定,最终导致无辜嫌疑人错误供述的风险大幅提高。
当然,需要谨慎的是,域外的上述认知-行为科学研究,其结论和应用前景也有值得进一步斟酌之处。
第一,就上述认知-行为实验本身而言,很多对警察辨别有罪/无辜嫌疑人的能力的测量均在模拟现场中实施,不具有真实审讯环境中的高度封闭性、对抗性及人身干预性。必须承认,运用真实环境来测试警察辨真能力存在着难以避免的限制:一方面,侦查讯问是刑事司法中最秘密的一个阶段,无论是从侦查效率,还是从保障隐私权的角度讲,真实案件的审讯过程都不太可能被用于行为实验,甚至同时兼顾行为实验的可能性也不大。另一方面,按照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三种模型划分:纯粹的程序正义(如,赌博),完善的程序正义(如,分蛋糕),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如,刑事司法),刑事司法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并不存在一种客观的裁判结果能够用于证明程序本身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到底谁是真正意义的犯罪人是不确定的。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谁在说谎,谁没说谎呢?此外,相关研究多以大学生为被试对象,用他们来研究审讯活动或犯罪追诉中辨别真伪的情况,实际上是代替了警察这一专业的审讯主体。学生被试无论是在年龄、资历、经验上都与警察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对辨识真假的测试中,可能有一些不可预知的变量卷入。还有不少研究是以大学生被试来模拟犯罪和被审讯者,而大学生与真正的罪犯之间也会存在较大认知过程、心理特征和人生阅历方面的差别,动摇实验结果的可信性。
第二,就对中国的启示而言,许多关于辨别真伪陈述的研究对某些表征说谎的行为,尤其是非言语行为变量加以测量。这种测试方法本身存在一定局限,因为非言词行为信息具有很强的文化性。同言语交流一样,非言语交流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和民族差异,不存在普适性的、能够表征说谎的行为变量。例如,在多数国家,微笑表征着淡定和轻松,但在日本,微笑可能恰恰是掩饰焦虑或不悦的一种习惯举动。至少,形成实验结论时,须要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若要使认知-行为研究对中国司法产生积极作用,还需以中国刑事审讯为语境,以中国罪犯和警察为被试进行研究,获得客观发现,并形成具有共识性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对于那些旨在提高警察辨真能力的实验结果,一些(如主动的、介入式的讯问技巧)可以尝试,另一些(如让讯问者暂时先不接触犯罪细节)尝试起来会有难度,更有其他一些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如对语言模式进行内容分析),实际尝试的成本较高,可行性也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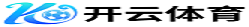
发表评论